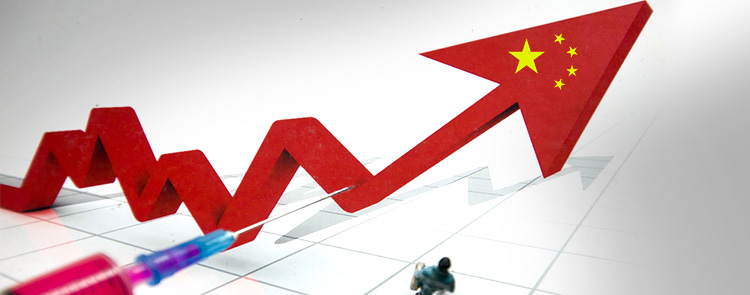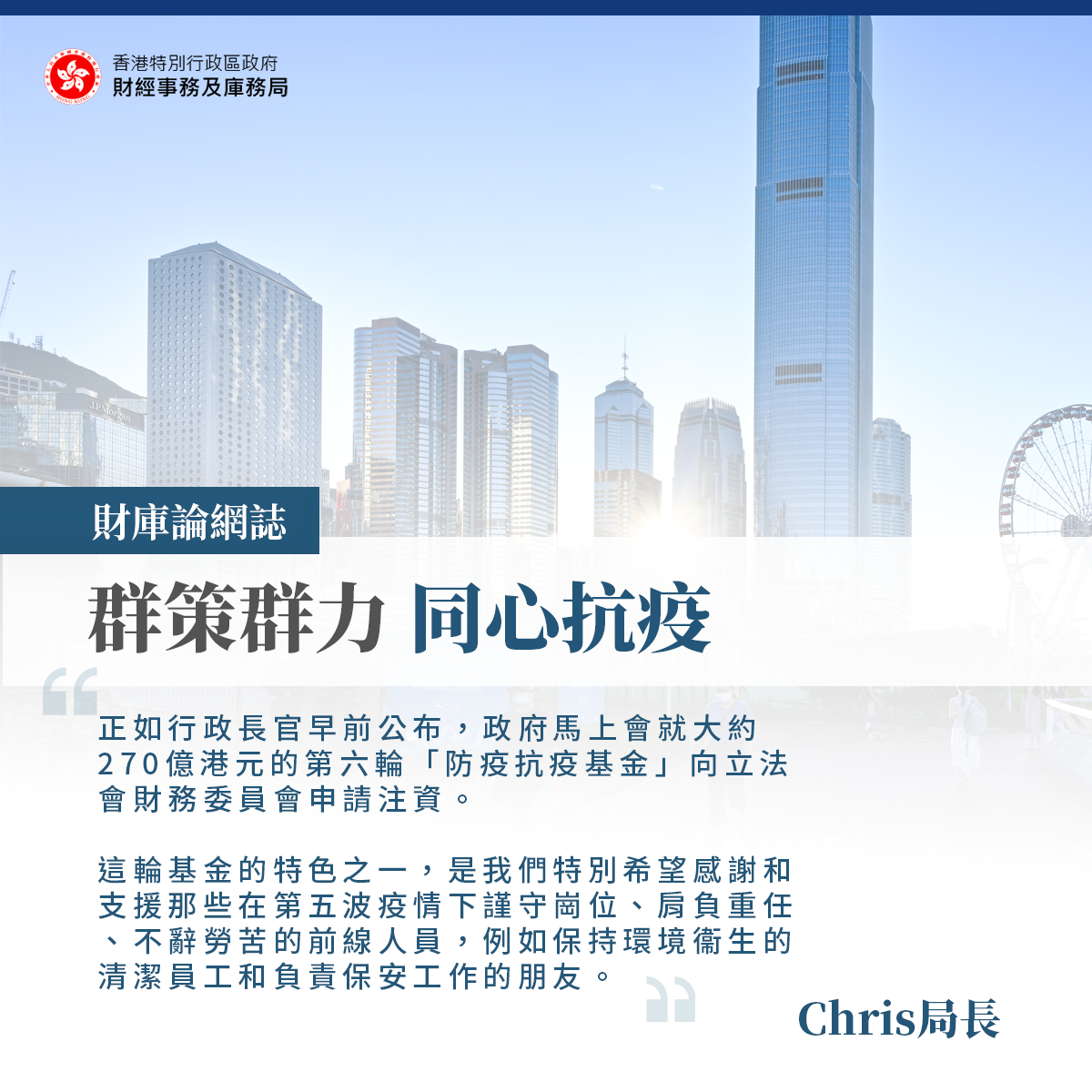歷史走到這一步 中國開始「平視」世界
田飛龍 北京航空航太大學高研院/法學院副教授

剛剛過去的2021年是「政治大年」,有建黨百年及其「第一個百年目標」的完成,有十九屆六中全會歷史決議作為「第三個歷史決議」的新時代奠基意義,有中美在貿易戰之外展開的全球民主大辯論,中國在美國普適價值的最敏感和最要害部位實施了意外的「戰略突擊」。
民主峰會恰似美國霸權的「夕陽紅」,紅則紅矣,近乎夕陽,也有幾許悲愴。中國民主白皮書及作為附篇的香港民主白皮書,則不僅標誌著中國民主的自成體系,也標誌著香港民主在「一國兩制」範疇尋找到了錨定國家體系的真正身份與方向感。
「愛國者治港」不是別的,等效於遲來的「去殖民化」,是愛國與民主在香港自治空間的有機結合,民主不再能夠被用於反國家和反法治。2019修例風波,香港反對派和外部勢力暴露了一切,為中央的撥亂反正提供了最完整和最精凖的病灶。有了香港國安法和新選舉法的香港,更加繁榮穩定。
中美無論是全球治理範疇的拉鋸還是香港平台的對抗,乃至台海的激烈衝突,都是中國在成長,美國在遏制。中國的成長無法遏制,且直到美國無力遏制,新的中美關係和全球秩序才會露出真容。這些年,美國只是在維護霸權,中國則是自主從容地成長。中美關係的一切煩惱根源於此。美國似攻實守,中國似守實攻。中國沒有拿走美國的任何東西,中國只是獲取自己應得的地位、尊重和利益。美國的「非分」霸權需要節制和限縮,中國的「正當」權利需要尊重和讓與,中國要到達應許的文明方位,並在這一進取過程中貢獻新的價值、規則和增量利益。中國的「一帶一路」和人類命運共同體是許給中華民族和人類未來的理想圖景。東方文化也有尊嚴,中國也有夢想的權利。
2021年也是新冠二年,「奧密克戎」(Omicron)所向披靡,繼續「嘲諷」著自由西方的原子化和民主社會協同的巨大漏洞。從西方對抗防疫管制的大規模示威與暴力中,從西方一流哲學家、法學家對疫情分析的錯漏百出中,我們似乎看到了反智與反諷的疊加。以「自由」掩飾「自私」,誤解東方文化與制度中的「家國」倫理和自律精神,並要求中國放棄「動態清零」的有效防控體系,這是東西方「文明衝突」在共同的防疫考驗中的別異與落差。香港的「通關」之痛也在於此。疫情暴露了西方文明的體質虛弱和價值反噬,反襯了中國文化與制度在保護人民與整體協同上的系統優勢。
西方要反思的,絕不僅僅是法蘭西斯·福山所謂的「政府能力」之低效或「否決政體」的疲象,而是現代個體主義的精神與意義挫折。與之相比,仍具有集體主義和共同體主義基礎和偏好的中國社會,則展現了面對大規模、持續化疫情的強大政府能力與社會韌性。西方現代性的極度解放與極致發揮,終於還是走向了秩序和理性的反面,中國則構成了恰當的參照和對比。
2021年3月6日,在全國兩會的講話中,習主席提及「平視」西方的論斷,是東西方關聯式結構性變革的一個縮影。「平視」所需要的絕不僅僅是勇氣,甚至不是蘇聯、德國、日本式的「強力」挑戰,不是「列強規範」下的霸權之爭,而是深植中華文化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和平發展之約,一種真正切合自身文明與人類共同利益的新關係模式。
 「平視」心態:中國在2021年裡說出了「美國沒有資格」這句話。
「平視」心態:中國在2021年裡說出了「美國沒有資格」這句話。
「平視」是一種歷史邀請,是一種釋放給國民和世界的善意:向內,邀請國民從精神上自立,堅定自身的文明自信和制度自信,走出近代以來對西方的或仇視或崇拜的極端化情結;向外,對「列強世界觀」和霸權主義說不,以和平發展核心價值觀與堅定有力的反制行動制衡強權與霸權,示範性建構真正平等化與相互尊重的新型大國關係,為「人類命運共同體」澄清規範基礎和互動法則。
中國之「平視」,不是新霸權的確立,而是新世界的發現和耕耘。與「美國治下的和平」及其霸權亂序相比,這個「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新世界恰似一個巨大的「歷史荒原」,有待各方的合意與耕耘。2022,我們當策馬於這一「平視」世界觀下的歷史荒原,敢於鬥爭,敢於建設,披荊斬棘,堅定前行。
這是一種世界觀與思維習慣的轉換,也是一場必然艱難困苦的精神鬥爭。西方將中國誤解為「第二個蘇聯」,是因為西方從未真正理解和尊重中國文化的天下尺度和生命倫理,也從未真正理解和尊重中國人民始於1840年的自主現代化道路的探索和堅守。西方只是習慣性地以為:東方的中國是專制、野蠻和落後的,是需要以西方的個人主義和自由民主範式加以改造的,是需要告別自身傳統而全盤西化的。
將中國改造為一個西式「民主」社會,絕不僅僅是一種西方「民主」福音的簡單移植和分享,而是有著深刻的文明征服和經濟支配意義:
其一,中國自身的文化和生活方式被否定,西方從改造中國過程中獲得無以倫比的道德和文化征服成就感,這是西方文明的虛榮和傲慢;
其二,中國或其分裂而成的多個政治體,以其市場、消費力和資源要素無條件供給西方的經濟生產體系及其利潤鏈條之需要,維持長期的剝削與支配關係。
其實,特朗普貿易戰和拜登的「民主」軟實力戰爭,根本目的仍在於逼迫中國就範:放棄政治生存和文化合法性,放棄經濟主權與國民經濟體系的自主性。美國的底層設問在於:中國版的「廣場協議」就那麼難嗎?以自由民主瓦解中國的政治自主性、民族主義和天下競爭倫理就那麼難嗎?中國難道是美國霸權體系的「例外」嗎?
是的,就是那麼難,因為這是在中國。「仰視西方」即便在中華民族近代苦難最深重之時,也只是一部分人的文化屈從和心理的「自我東方化」,而絕不是民族精神的整體性選擇。新文化運動中的「問題與主義」之爭,其本質在於中國的現代化要不要有自身的文明根基和方向感,以及用什麼樣的方法和路徑達成中國自己的現代化。中國共產黨的100年,其歷史本質就在於回答這一個關鍵性問題,並找到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即馬克思主義的中國民族形式這樣的科學道路。
2021年,在中共十九屆六中全會決議中,在中國自身的文化與制度自信更加充分的條件下,中央又提出了「兩個結合」論,即馬克思主義不僅要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還要與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這是有精神突破意義的:即便面對馬克思主義的真理體系,中國也不僅僅是問題和場域的「實踐」載體,還是文化和文明的規範基礎。一句話,中國本身也是真理來源,是有資格與馬克思主義結合的偉大文明。中國回到自身,中國重新生長,這是令人驚奇和驚喜的。
中國的文化形象與世界形象,不是被妖魔化的「惡龍」,不是有著歧視意蘊和東方主義審美偏執的「眯眯眼」,不是仍由西方進行博物館式文化賞玩或人類學式種族獵奇的東方野蠻國度,而是堂堂正正的中華文明及其現代形象。
而為中國之正常形象賦予尊嚴和集體人格的,是中國人民及其領導力量中國共產黨。中國憲法序言之「中國各族人民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不只是一種格式化修辭,更是一種實在的主權組織形式與人格化。毛主席說過,組織起來的中國人民是惹不得的。抗美援朝時美國惹過,後來的印度、蘇聯、越南都惹過,都碰壁了。現在的美國繼續在「惹」,不僅有貿易戰,還有科技戰、金融戰和軟實力戰爭,是一種「戰略競爭」,其本質是一種「戰略冷戰」。幸好,中國人民組織起來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持續存在且不斷理性化。
2021年7月1日上午,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大會在北京天安門廣場隆重舉行。
在與美國進行體系鬥爭的過程中,中國的大國成長在進行著一種獨特的「學習」過程,不是全盤西化的「學習」,更像一種「師夷長技以制夷」的精准區分性的學習。洋務運動是中國應對西方挑戰的第一次思想自覺和實踐努力,儘管在現代化的初期有著各種各樣的缺陷和失敗,但其所提出的「中體西用」、「師夷長技以制夷」的本體自信和技術理性化的觀念和方法,在今天我們重歸中國自信的新時代條件下,反而有了更多的相似性和正確性。
當然,這種相似不是歷史的倒退,而是經由「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確立中國自身地位和道路後展開的歷史檢討和歷史進步。我們今天的精神狀態更加健康和從容,我們不再「自賤」,也不將西方視為「蠻夷」,而是一種訴諸現代平等精神的「平視」,我們要做自己,但不封閉自己,而是以我為主,開放吸納,吞吐自如。
一些缺乏「溫情與敬意」、「同情的理解」以及大歷史觀眼光與政治存在意志的人,容易將新時代試圖確立的、堂堂正正的中國文明和中國制度視為中國歷史某個形象的複歸,或者用諸如蘇聯、德國、日本之類的某段歷史形象加以簡單而機械的套用,以貌似深刻和歷史教誨的心態「訓斥」貶低新時代的飽滿意志和取向,實在是「燕雀」之類或「驚弓之鳥」罷了。
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乃是「兩個結合論」意義上具有世界歷史意義的新文明現象,絕不是「王道復古」或封建復辟式的回歸,也不是某個外國個案的歷史重複,而只能是中國文明與制度的自我定型和成熟。面對中國的自我定型,一切誤解中國偉大文明與政治創造性的人,無論西東,都會失算和失望了。
當然,這種在民族復興航船桅杆上眺望到的未來歷史與前景,以及基於文化自信和哲學見解而作出的超前判斷,並不能代替中國當下千難萬險的內外建設處境和鬥爭慘烈過程。甚至,越是走向世界舞臺中央,越是登近世界歷史巔峰,內外風險與精神困頓就越是濃重,而且分寸、智慧、定力和進取心的歷史考驗就愈加凸顯。
當我們由「仰視」調校為「平視」,我們看到了一個新的世界影像,但卻尚未從哲學和政治本質上真正抓牢這個影像。作為影像的民族復興和人類命運共同體,並無具體的歷史力量給出絕對的實現承諾,而是必須依靠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組織起來」並集體行動,堅定前行。
2022,必然是風險疊加飆升的一年。對新時代之中國的內外建設與戰略進取而言,結構性挑戰和壓力是必然存在的,至少包括但不限於:
其一,國家治理體制的有機性和團結程度。偉大事業,要「治法」,也要「治人」。全面從嚴治黨和全面依法治國是制度層面的調整和準備,已有重要而持續的進展。但高層決斷與官僚層梗阻懶政之間的制度性摩擦和執行成本飆升的風險始終存在並可能擴大。如何從思想和制度上解決真正的文化自信和責任倫理問題,形成中國管治精英層牢固的政治團結和力量整合,是「治人」層面的核心挑戰。
其二,集體價值和個體價值的平衡及其維持。民族復興的宏大敘事與動員管制體制,如何與現代性條件下個體權利、尊嚴和多元化價值之間形成可預期和可理解的平衡,形成既團結緊張又嚴肅活潑的生動公共秩序,增強社會韌性和包容性,給個體自由與個人人格以適當而確定的空間,是新時代體制與人心磨合層面的核心挑戰。這方面的公共事件仍不斷發生,制度和公共官員的回應治理仍未臻成熟和理性化,需要持續精細地檢討和改革,以及增強監督問責的執行力,使民心信服,並阻斷外力有間。
其三,國家統一與「一國兩制」範疇的分離風險和挑戰。「一國兩制」範疇的挑戰不會止步於香港國安法和新選舉法,也不會因為制裁立陶宛和減少台灣「邦交國」而降低。港澳治理如何精細而微妙地落實「愛國者治理」根本原則與制度性要求,維持愛國大前提與認同以及港澳社會既有活力和自由體系之結構平衡,分寸和智慧需要磨合提煉。對台灣則需要謀定而後動,需要依據憲法和反分裂國家法「兩條腿」走路,既避免冒進錯失,又避免裹足不前,要主動作為以求突破。
其四,來自美國與西方的「新冷戰」的激進演變和挑戰。真正的外部體系性風險始終不能低估和放任。拜登的戰略競爭的本質是特朗普+,是戰略冷戰。中美的根本競爭不是利益之爭,而是制度和價值之爭,是在爭「天下」。我們的戰略意志和戰略相持階段的全方位準備仍嚴重不足。
其五,技術卡脖子和經濟體系「脫鈎」的壓力始終存在。這一方面考驗中國科研體制改革與創新的尺度及活力,另一方面則取決於中國和外部經濟體互聯互通的程度及信任度。這是對中國科研、技術、生產、外交與全球化存在的全面挑戰,當然也是國家成長的戰略契機。
其六,「一帶一路」與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實質性進展和制度性增量。這是中國走向世界舞台中央的戰略生命線,是中國外向型經濟體系和制度合作體系的實踐場域。我們必須在市場、文化、社會、制度與治理體系間尋求完整的謀劃和進展,不能唯利是圖,不能自以為是,不能好大喜功,不能孤立和碎片化建設,不能遇到困難挫折就一撤了之,而需要精細化佈局及建立完整的風險管理和法律規制系統,資本合作與制度合作相結合,增強外部建設的抗壓能力和制度化保障水準,並加大涉外法治立法和執法體系的建構。
總之,2022是對2021既有政經議題和風險的繼續,也是中國在內外建設和制度風險應對方面謀求結構性方案和體系性成果的關鍵一年。「平視」是中華民族整體的轉身和定位,是東方文化和制度的自我確立,更是民族復興和人類命運共同體建構的應許身段和姿態。「平視」立不立得住,新時代精神可否自成體系和內在融洽,中國的內外建設可否相互支撐與整體協調,新世界願景和秩序能否在中國參與下破繭而出,2022是關鍵,也是歷史機遇!
原文連結:觀察者網